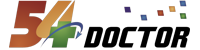媒體朝陽
北京日報/2013/05/07/“不急”的急診病人
下午4點多,120急救車剛送進來一位滿頭白發的女患者,120急救醫生和患者家屬正圍著朝陽醫院急診分診臺的兩名護士交代病情,一個護士在病人的病歷上快速地記錄,另一位護士將一個紅色圓形標記貼在病歷本上,準備把病人往搶救室送。
正忙得不可開交之時,一位50出頭的男士溜達到分診臺前:“護士,我要看病。”
護士抬頭看了他一眼——真正的急診病人,大多數不是被平車推進來的,就是被家屬攙進來的。可眼前這位,看上去挺健康。
“你怎么不好?”
“咳嗽,兩周多了,不發燒。”
“先去那邊窗口掛個號,然后等著大夫叫號。”護士拿出手機看了一眼時間,跟同事小聲嘀咕了一句:“這哪兒用看急診?!肯定是在門診沒掛上號,就奔咱們這兒了。”
趁著候診,記者跟這位男士一攀談,還真被護士猜著了。“我是來看門診的,路上太堵,4點才到,早沒號了。我可是倒了兩趟公交折騰了快兩個小時才趕過來的,不能白來一趟啊,看個急診開點兒藥也成啊。”
其實,像這位男患者一樣“不急”的急診病人還真不在少數。
“現在還不是高峰,晚上七八點鐘的時候,急診里‘不急’的病人更多。好多人都是晚上下了班以后來急診看病的。”有一位老護士很有經驗。
曾經有人在北京部分醫院做過調查,在急診接診的患者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病人不需要看急診。各醫院急診科雖然都有相應的就診標準,但形同虛設——在當今的醫患環境下,只要病人來了,急診醫生就不能拒絕。就是因為這些“不急”的急診,使真正應該看急診的病人等候時間被拉長。
第二天凌晨1點多,記者再次來到分診臺時,又碰上了一位“不急”的患者。
這是一位40多歲的中年女士。“我晚上失眠,有小半年了,今天晚上又睡不著了,吃了藥都不管事。”問她為什么不白天來,這位女士回答:“我也不是總失眠,白天想不起來看病。反正我住得離這兒也不遠,過來看看醫生能不能給我換種藥。”
正說著,分診臺又來了三四位操著外地口音的男子,都明顯喝高了,其中一位被同伴架著還不停往下出溜。醫生過來檢查發現只是醉酒,身體沒有其他問題,不需要治療。但這名男子的同伴大聲嚷嚷著,一定要輸液。
“這是對急救資源的浪費!”一位急診大夫忿忿地說,普通感冒、醉酒和一些慢性病占用了有限的急診資源,很可能會延誤真正急診患者的救治時間。
在美國和加拿大等國家,如果是輕癥患者看急診,往往要等候很長時間,急診優先搶救重癥患者。目前,協和醫院、朝陽醫院不得不對急診患者的病情進行初步評估:危重癥貼紅標,直接送搶救室;黃標為普通急診患者,需要盡快治療;綠標為輕癥可以等候。貼紅標的病人都被直接通過綠色通道送進了搶救室,最令大夫們糾結的,是普通急診病人和非急診病人,因為根本無法按輕重緩急來分診。
“哎哎哎,我們先來的,憑什么他們先看啊?!”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闖進急診內科診室責問醫生。
“這位老太太八十多了,頭暈心慌,我們擔心她心臟有問題,先給她做個檢查。”
“來看急診的誰不急呀?我爸也六十多了,正難受著呢,講不講先來后到啊!”小伙子不依不饒。
“這種事幾乎每天都能遇到。我們也沒辦法,按理說應該讓病情重的先看,但為這事老鬧糾紛我們也受不了,所以基本都是按順序來,如果有人覺得特別難受想提前看,我們只能讓家屬互相協商。”
也許,只有當急診科里都是真正的急病人,擁擠嘈雜的急診室才能找回與生命賽跑的分秒必爭和永不放棄。而這,不僅需要制度上的保障,更需要患者就醫素養的提高。
記者手記
在北京急診量最大的朝陽醫院急診科的掛職蹲點即將結束,3個多月的零距離接觸,讓我漸漸看到了一個個故事背后的深層背景和復雜原因。在我國,急診醫學剛過“而立之年”。30年前,我國第一個急診科在北京協和醫院成立,建科時每天接診的患者只有六七十人;而現在,每天接診患者高達六七百人。一個新學科的迅猛發展,必然伴隨著各種問題的出現。6篇報道,不可能完整展現醫院急診室這個小社會,僅希望能讓公眾多一些了解,進而多一份理解。
師傅點評
北京日報記者方芳以普通人的視角,通過對急診診療過程的觀察,發現了很多在我們看來習以為常的事情,卻蘊藏著豐富的哲理。
醫患關系的緊張,需要多方面多角度的關注。她這6篇報道,反映了目前急診診療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問題,也沒有回避我們面臨的困難和困惑。對于普通民眾加深對急診的了解,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和途徑。
記者以第三方身份,加入到醫患之間,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為營造和諧的就醫環境會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希望這樣的報道常態化。
——北京朝陽醫院急診科主任醫師何新華 (原標題:“不急”的急診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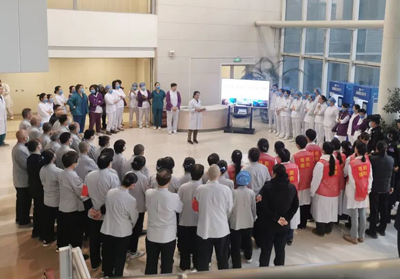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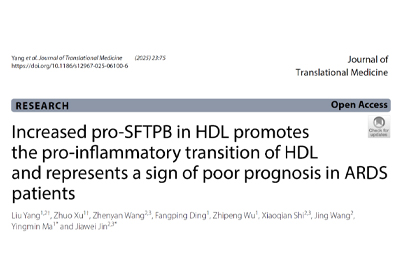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11010502033042
京公網安備11010502033042